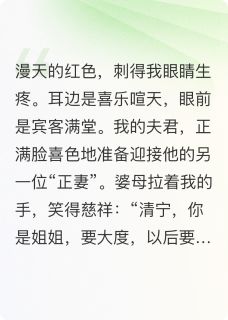漫天的红色,刺得我眼睛生疼。耳边是喜乐喧天,眼前是宾客满堂。我的夫君,
正满脸喜色地准备迎接他的另一位“正妻”。婆母拉着我的手,笑得慈祥:“清宁,
你是姐姐,要大度,以后要和妹妹好好相处。”大度?我记起来了。前世,我就是太大度,
才落得个幼子被那毒妇害死,自己被污蔑失德,一杯毒酒赐死的下场。而他们,
踩着我们母子的尸骨,一家和美,子孙满堂,享尽荣华。重生回这一刻?好,好得很!
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,我缓缓起身。端起桌上那杯给新人的合卺酒。然后,
狠狠地、一字一句地,泼在了婆母那张伪善的脸上!“兼祧?我呸!”“今天,
谁也别想进这个门!”“我疯了,不信你们就试试!
”1冰冷的酒液顺着婆母保养得宜的脸颊滑落,滴滴答答,砸在她华贵的寿字纹锦袍上。
满堂的喜乐,戛然而止。所有的目光,瞬间聚焦在我身上,震惊、错愕、愤怒,不一而足。
婆母,永宁侯老夫人,一辈子都在京城贵妇圈里要脸面的人,此刻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,
那份伪装出来的慈祥彻底崩裂,只剩下狰狞。“沈清宁!你疯了?!”她尖利的声音,
划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。我的夫君,永宁侯世子陆景渊,
也终于从他那“喜得两妻”的美梦中惊醒。他快步冲到我面前,一把抓住我的手腕,
力道大得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。“清宁!你这是在做什么!快给母亲道歉!
”他的眼中满是失望和愠怒,仿佛我是一个无理取闹的疯妇,
打碎了他“齐人之福”的完美画卷。我看着他,这个我爱了一辈子,也恨了两辈子的男人。
前世,他也是这样,在我幼子高烧不退,求他去请太医时,
他却陪着他的“真爱”刘如玥赏雪作诗。他说:“清宁,你不要这么小心眼,玥儿身子弱,
吹不得风。”结果,我的孩儿活活烧坏了脑子,缠绵病榻数月后夭折。而刘如玥,
不过是打了个喷嚏。道歉?我笑了。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“道歉?”我抬起另一只手,
狠狠地甩开他的钳制。“陆景渊,该道歉的人是你们!”我的目光如刀,扫过他,
扫过我那面色铁青的婆母,最后定格在门口那顶即将进门的喜轿上。“我沈清宁,
乃镇国公府嫡女,明媒正娶的永宁侯世子妃。”“你们,一个所谓的夫君,一个所谓的婆母,
却要在我还活着、还好端端地站在这里的时候,再迎一房‘平妻’进门。
”“你们将我沈家的脸面置于何地?将大周的礼法置于何地?”我声音不大,却字字清晰,
掷地有声,响彻整个喜堂。“兼祧?真是好一个遮羞布!”“说白了,
不就是你陆景渊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,看上了那个清倌人出身的刘如玥,
又舍不得我沈家的权势和嫁妆,才想出的这等龌龊法子吗!”“无媒苟合,本就下作!
如今还想披上‘兼祧’这层皮,让她登堂入室,与我平起平坐?你们永宁侯府的脸,
是金子做的吗?这么大!”一番话,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,狠狠扇在陆家母子的脸上。
满堂宾客,瞬间哗然。清倌人出身!这三个字,像是一道惊雷,炸得所有人都头晕目眩。
陆家对外宣称,这刘氏女是远房宗亲的孤女,品性高洁。可如今被我当众揭穿,
那层遮羞布算是彻底被扯了下来。陆景渊的脸,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
“你……你胡说八道什么!”“我胡说?”我冷笑一声,从袖中摸出一张纸,
狠狠甩在他脸上。“这是你半月前在醉仙楼为她赎身时签下的文书,上面你陆大世子的印鉴,
还新鲜着呢!”“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?陆景渊,你当我是死的吗!
”2陆景渊看着脚下那张轻飘飘的纸,却觉得有千斤重,烫得他不敢去捡。
婆母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,她到底是经过大风大浪的,立刻厉声呵斥,试图夺回场面。
“住口!你这个妒妇!”“我们陆家因你无后,才不得已行兼祧之策,延续香火。
你不思感恩,反倒在此撒泼,简直毫无妇德!”她搬出了“无后”这座大山。
这是压在古代女子身上最重的一道枷锁。前世,我也曾为此自责不已,觉得是我肚皮不争气,
才给了他们羞辱我的理由。可现在,我只觉得可笑。“无后?”我看向陆景渊,
眼神里满是嘲讽。“我嫁入陆家三年,你扪心自问,有几个晚上是在我房里过的?
”“不是去书房‘苦读’,就是去和你的‘红颜知己’吟诗作对,偶有几次留宿,
也是喝得酩酊大醉!”“我如何有孕?靠这满堂的喜气吗?”我的话露骨又直白,像一把刀,
剖开了陆景渊那“君子”的伪装。他脸上血色尽褪,嘴唇哆嗦着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席间一位与陆家交好的老御史站了出来,捻着胡须,摇头晃脑地教训我:“世子妃,
纵然心中有怨,也不该在今日如此失仪。兼祧虽不合常理,但乃孝道之举,你身为正妻,
当以夫家为重,以孝为先……”“孝?”我直接打断他的话,目光如炬。“这位大人,
敢问您读的是哪朝的圣贤书?我大周《礼典·婚嫁篇》写得清清楚楚:‘娶妻以礼,
绝无二嫡’。何曾有过一门两正妻的说法?”“至于兼祧,更有严苛规定:须得宗族无继,
报备宗正寺,由族中长老与官府共同见证,择旁支子嗣过继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
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,自创一个‘平妻’的名头来混淆视听!”“你们这不叫兼祧,
这叫淫祀!是乱家之举,败德之行!要被刻在族谱上,让后世子孙唾骂的!
”我这一番引经据典,有理有据的话,直接把那老御史怼得满脸通红,哑口无言。
他支支吾吾半天,只能甩袖坐下,嘴里嘟囔着“悍妇,悍妇”。我根本不理他。我的目光,
再次锁定了我的婆母。“婆母,您口口声声说为了香火,那我倒要问问您。”“我嫁妆里,
那三十六抬专门给陆家子嗣准备的赤金长命锁、和田玉平安扣,
你们是不是已经提前给了门外那位?”“我库房里,
那些给我未来孩儿准备的虎头帽、百家被,是不是也被你们悄悄搬空,送去讨好新人了?
”婆母的眼神闪烁,不敢与我对视。我心中冷笑。前世的记忆涌上心头。我的孩儿出生时,
他们说府里开销大,一切从简。而刘如玥的孩子,一出生便被金山银山围着。那些,
本都该是我的孩儿的!想到这里,我心头的恨意几乎要冲破天际。3我的质问,
让陆家母子彻底陷入了被动。他们没想到,一向温顺隐忍的我,会变得如此伶牙俐齿,
如此……疯狂。“够了!”陆景渊终于爆发了,他一把抓起地上的赎身契,撕得粉碎。
他双目赤红地瞪着我,仿佛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。“沈清宁,你到底想怎么样?
”“就算玥儿出身不高,可我是真心爱她!我娶她,与你何干?你依然是世子妃,
你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!”“我陆家给你荣华富贵,给你尊崇地位,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?
”听到这话,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不是因为他所谓的“真爱”,而是因为他那理所当然的**。
“我的地位?”我指着门口的喜轿,一字一句地问他:“我若接受了她,我的地位在哪里?
在京城所有贵妇的同情和嘲笑里吗?”“我的荣华富贵?”我指着这满堂的富丽堂皇,
“陆景渊,你看清楚,这侯府能有今日的体面,有多少是我沈清宁的嫁妆撑起来的?
你花的每一分钱,都沾着我沈家的光!”“你用着我的钱,养着你的外室,
如今还要让她登堂入室,与我平起平坐,分享我的一切?陆景渊,是谁给你的脸!
”我的声音,凄厉而尖锐,带着前世所有的不甘与血泪。“你想要她,可以!”“今天,
我给你这个机会!”在所有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,我一步步走向大堂中央。那里,
摆着一张铺着红绸的香案,上面放着给新人的信物——一对龙凤呈祥的玉佩。
那是陆家的传家宝。前世,他们逼着我,亲手将象征着“凤”的那一半,交到了刘如玥手上。
那一刻的屈辱,我永生难忘。这一世,休想!我走到香案前,拿起那对玉佩。
陆景渊脸色一变,急忙喊道:“清宁,不可!”我回头,对他粲然一笑。那笑容,
妖冶又疯狂。“陆景渊,看好了。”下一秒,我双手用力,狠狠地将两块玉佩对撞在一起!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!那对价值连城、寓意吉祥的传家宝,瞬间碎成了几块,散落在地。
满堂宾客,倒吸一口冷气。所有人都被我这惊世骇俗的举动吓傻了。我扔掉手里的碎玉,
仿佛丢掉什么垃圾。然后,我转身,一步步走向门口。喜娘和丫鬟们想拦我,
却被我眼中的狠戾吓得连连后退。我走到那顶精致华美的喜轿前。轿子里的刘如玥,
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,轿身微微晃动。我没有理会她。我只是伸出手,
抚摸着轿身上那大红的喜绸。然后,猛地一用力!“刺啦——”一声裂帛的巨响,
那崭新的喜绸,被我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!一下,两下,三下……我像是疯了一样,
将轿子上的所有装饰,所有喜庆的红色,全都撕得粉碎!还不够!
我看到旁边为了迎亲准备的火盆,里面炭火正旺。我抓起一把破碎的喜绸,想也不想,
直接扔了进去!火苗“轰”的一声窜起老高。“沈清宁,你这个疯子!”陆景渊冲过来,
想要拉开我。我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,从头上拔下那支代表着世子妃身份的金步摇,
用尖锐的一端,对准了自己的脖颈。“别过来!”我厉声尖叫,眼神里是同归于尽的决绝。
“今天,有我没她,有她没我!”“你们永宁侯府,是想要一个疯死的镇国公府嫡女,
还是想要一个干净利落的和离妇?”“你们自己选!”4我的威胁,像一把利剑,
悬在了陆家所有人的头顶。一个“疯死”的镇国公府嫡女。这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镇国公府将与永宁侯府不死不休。我爹是手握兵权、威震四方的镇国公,
我大哥是禁军统领、天子近臣。他们若要追究,小小的永宁侯府,根本不够看。陆景渊的脸,
白了。婆母的身体,晃了晃,差点瘫倒在地。他们千算万算,
没算到我会用自己的命来当筹码。前世那个温顺的沈清宁,已经死了。
死在了他们的无情和算计里。现在站在这里的,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回来的恶鬼!“清宁,
你……你先把步摇放下,有话好好说。”陆景渊的声音软了下来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。
“好好说?”我冷笑,“事到如今,还有什么好说的?”“陆景渊,我只问你一句,这婚,
你离不离?嫁妆还不还?”他看着我,眼神复杂,有愤怒,有不甘,还有一丝……后悔?
后悔?太迟了!“我……”他还在犹豫。我手中的金步摇,又往前送了一寸。一丝血迹,
顺着我白皙的脖颈流下,触目惊心。“我数三声。”“三!”“二!”我的声音冰冷,
不带一丝感情。“我离!”在我数到“一”之前,陆景渊应承了下来!5“清算嫁妆?
”婆母尖叫起来,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。“沈清宁,你别欺人太甚!你嫁入我陆家三年,
吃穿用度,哪一样不是陆家的?现在还想把嫁妆一分不少地拿回去?做梦!”“哦?
”我笑了,笑得愈发冰冷。“婆母这话说的,倒像是我占了你们陆家多大的便宜。
”“既然如此,那我们就好好算算!”我扬声道:“采荷!”我忠心耿耿的陪嫁大丫鬟采荷,
立刻从人群后方走了出来。她手里,捧着一本厚厚的册子。那是我当年十里红妆的嫁妆单子。
“采荷,念!”“是,**!”采荷清了清嗓子,朗声念道:“镇国公府嫡女沈氏清宁,
嫁妆计有:”“京郊良田五百亩,南街旺铺三间,玉器行一间,
绸缎庄两间……”“赤金头面二十套,南海珍珠一百二十颗,东海血珊瑚摆件一对,
前朝王羲之真迹《平安帖》一幅……”“压箱底现银,十万两!”采荷每念一句,
堂上宾客的脸色就变一分。当念到“十万两现银”时,满堂皆是倒吸冷气的声音。
这哪里是嫁妆?这简直是搬来了一座金山!众人都知道镇国公府疼女儿,却没想到,
竟然到了这个地步。永宁侯府这几年的风光,怕不是全靠这嫁妆在撑着?婆母的脸,
已经从铁青变成了死灰。陆景渊更是面无人色。我看着他们,缓缓开口:“这些,
只是嫁妆单子上的明数。”“我嫁入陆家三年,这些田地铺子的收益,少说也有五万两银子。
这些银子,全都贴补了侯府的用度,账目可都清清楚楚地记在内院账房里。”“还有,
为了给世子爷打点官场,我从我私库里,拿了三万两银票,送去了吏部王侍郎府上,这件事,
世子爷不会忘了吧?”陆景渊的嘴唇,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。我步步紧逼:“现在,
我要和离。”“嫁妆,一分一厘,我都要带走。这三年的收益,五万两,你们要还给我。
我为你仕途铺路的三万两,也要一并还来!”“另外,”我顿了顿,眼神如刀,
“我沈清宁的清白名声,被你们如此践踏,总得有个说法吧?”“精神损失费,不多要,
就算你们五万两。除了前面说的那些,现银方面凑个整数,你们陆家,
一共该还我二十三万两白银!”“至于我这三年在你们陆家的吃穿用度,就算我赏你们的!
”“噗通!”婆母再也撑不住,一**跌坐在了椅子上。二十三万两!
还有良田、旺铺…这简直是要了永宁侯府的命!把整个侯府卖了,也凑不出这么多钱!
陆景渊指着我,气得浑身发抖:“沈清宁……你……你好狠的心!”“狠?”我仰天大笑,
笑声中带着无尽的悲凉。“我再狠,也比不上你们的心!”“我前世……不,
我以前对你们掏心掏肺的时候,你们是怎么对我的?”“陆景渊,是你自己说的,
是我痴心妄想,是你自己选的刘如玥!”“现在,你又有什么资格说我狠?”“求仁得仁,
这都是你们自找的!”6就在堂上陷入一片死寂,陆家母子被我逼得走投无路之时。
一声通报,如平地惊雷,炸响在侯府门口。“镇国公府大公子,沈威,到——!”话音未落,
一个身穿玄色飞鱼服,腰佩长刀,身姿挺拔如松的男人,已经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。他身后,
跟着一队披坚执锐的禁军亲卫,个个煞气腾腾,眼神如鹰。喜庆的永宁侯府大堂,
瞬间被一股肃杀之气笼罩。来人,正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大哥,沈威。大哥一进门,
目光便如利剑般扫过全场,最后,定格在我脖颈那道刺目的血痕上。他瞳孔骤然一缩,
周身的煞气,瞬间暴涨!“清宁!”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我面前,看着我的伤口,
声音都在发颤。“谁干的?!”我看到大哥,强撑了许久的坚强,瞬间崩塌。眼泪,
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前世,我被赐死之时,大哥正在边疆浴血奋战。等他得胜归来,得到的,
却只有我的一座孤坟。我魂魄看着他,永远忘不了,他跪在我的坟前,那个顶天立地的男人,
哭得像个孩子。这一世,我终于又见到了他。“哥……”我哽咽着,
将手中的金步摇扔在地上,扑进了他的怀里。“哥,他不要我了。”“他要娶别的女人,
他们逼我……”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将所有的委屈和恐惧,都在这一刻宣泄了出来。
沈威抱着我,高大的身躯气得发抖。他轻轻拍着我的背,声音却冷得像冰。“别怕,有哥在。
”他安抚好我,缓缓转过身,那双在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眼睛,死死地盯住了陆景渊。
“陆景渊。”他一字一顿,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。“我妹妹脖子上的伤,是你逼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