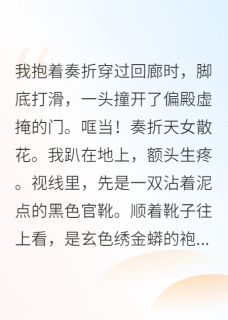齐珩还没到。
我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。
刚坐下,就听见那几个富商在小声议论。
“这位……就是那位沈大人?”
“看着年纪不大啊……”
“听说……跟王爷关系匪浅?”
“嘘!慎言!没看王爷都让他来作陪了?”
我如坐针毡。
恨不得把脸埋进地缝里。
脚步声传来。
齐珩到了。
他换了身墨蓝色常服,少了几分威严,多了几分矜贵。
富商们立刻起身,谄媚地行礼:“参见王爷!”
“免礼。”齐珩在主位坐下,目光扫过众人,最后落在我身上。
“沈大人也到了?坐本王旁边。”
一句话,让所有富商的目光,再次聚焦到我身上。
带着震惊和了然。
我硬着头皮,在齐珩右手边的位置坐下。
如芒在背。
酒菜上齐。
齐珩举杯,语气随意:“今日请诸位来,一为小聚,二来,江南水患,灾民嗷嗷待哺。朝廷虽竭力赈济,奈何杯水车薪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缓缓扫过那几个富商。
“在座诸位,皆是我大雍栋梁,家业丰厚。值此危难之际,不知可愿为国分忧,慷慨解囊?”
富商们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。
互相交换着眼色。
盐商胡老板率先开口,一脸愁苦:“王爷体恤灾民,我等感同身受!只是……唉,这两年生意实在难做!盐税又重,小人也是捉襟见肘啊!”
米商陈老板立刻附和:“是啊王爷!粮价飞涨,那都是本钱太高!小人囤积点粮食,也是为了让百姓在青黄不接时有口吃的!实在是……有心无力啊!”
绸缎商李老板更是唉声叹气:“关外商路断绝,绸缎积压,小人每日亏损,愁得头发都白了!”
三人一唱一和,哭穷哭得情真意切。
我冷眼看着。
这些老狐狸,一个比一个能装。
齐珩端着酒杯,静静听着。
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等他们哭诉完了,他才慢悠悠地开口。
“是吗?看来诸位,确有难处。”
富商们连忙点头如捣蒜:“是啊王爷!难!太难了!”
齐珩放下酒杯,指尖轻轻敲着桌面。
“本王向来体恤商贾不易。既然诸位手头紧……”
富商们脸上刚露出一丝喜色。
齐珩话锋一转。
“那本王,就给诸位指条生财的明路。”
富商们一愣。
齐珩看向我:“沈大人,户部前日清查旧档,是不是查出些……有趣的东西?”
我脑子嗡了一下。
户部旧档?
什么有趣的东西?
齐珩眼神平静地看着我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提醒。
我猛地想起,前几天在户部堆积如山的旧档里,好像翻到过几份前朝盐铁转运的旧账,里面有些猫腻……
难道王爷指的是那个?
我手心冒汗。
王爷这是要唱红白脸?让我当恶人?
我深吸一口气,硬着头皮开口。
“回王爷,确有此事。下官在清查前朝旧档时,发现一些……盐引、粮引的发放记录,似乎……有些不清不楚。”
我故意说得含糊。
那几个富商的脸色,瞬间变了。
尤其是盐商胡老板,脸都白了。
前朝旧事,真要深究起来,拔出萝卜带出泥,谁都不干净!
齐珩“哦”了一声,尾音拖长。
“不清不楚?”他端起茶杯,慢条斯理地撇着浮沫,“沈大人,你掌管户部档案,职责所在,可要查清楚些。若有疑问,不妨……请胡老板他们,协助调查?”
“协助调查”四个字,他说得轻飘飘。
落在胡老板他们耳中,却如同惊雷。
李老板反应快,立刻站起来,端起酒杯。
“王爷!小人虽不才,但忧国忧民之心拳拳!江南水患,百姓受苦,小人看在眼里,痛在心里!小人愿捐白银……五千两!助朝廷赈灾!”
陈老板也赶紧站起来:“小人愿捐米粮一千石!”
胡老板一咬牙:“小人……小人捐盐引五百引!”
齐珩没说话。
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只是继续慢悠悠地撇着茶沫。
花厅里死寂。
我手心全是汗。
胡老板额头也见了汗。
他一跺脚,像是下了狠心:“王爷!小人再捐白银……一万两!”
齐珩终于抬眼。
目光淡淡扫过三人。
“诸位拳拳报国之心,本王甚慰。”
他放下茶杯。
“沈大人。”
“下官在!”
“记下。胡老板捐白银一万两,盐引五百引;陈老板捐米粮一千石;李老板捐白银五千两。明日,让他们把东西,送到户部衙门。”
“是!”我赶紧应下。
“另外,”齐珩站起身,掸了掸衣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,“前朝旧档,年代久远,鱼龙混杂。沈大人,查不清楚的,就算了。不必深究。”
胡老板三人如蒙大赦,连连作揖:“谢王爷体恤!谢王爷体恤!”
齐珩点点头,看向我:“沈大人,替本王送送几位老板。”
“是!”
我送那几个惊魂未定、又肉痛不已的富商出去。
走到门口,胡老板擦着汗,偷偷塞给我一张银票。
“沈大人!一点心意!今日……多谢您在王爷面前美言!前朝旧账……”
我像被烫了手,赶紧把银票塞回去。
“胡老板!使不得!下官只是据实禀报!王爷明察秋毫,自有公断!”
胡老板讪讪地收回银票,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
“沈大人……前途无量!前途无量啊!”
送走富商,我回到花厅。
齐珩还坐在主位,正看着窗外。
烛光映着他半边侧脸,明暗不定。
“王爷。”我恭敬行礼。
“人送走了?”他没回头。
“送走了。”
“银票没收?”
我心里一紧:“下官不敢!”
他终于转过身,看着我。
“不敢?”他唇角似乎勾了一下,“是嫌少,还是怕烫手?”
我低头:“下官以为,此风不可长。”
“哦?”他饶有兴致,“说说看。”
“王爷今日设宴,恩威并施,既为赈灾筹得钱粮,又敲打了他们,使其不敢再过分盘剥。此乃高明之举。”我斟酌着词句,“若下官收了这银票,便是私相授受,坏了王爷苦心经营的规矩。也……污了王爷清名。”
他沉默片刻。
“清名?”他轻轻嗤笑一声,带着点嘲讽,“本王在朝野,还有那东西?”
我哑然。
确实,摄政王齐珩,在朝野名声毁誉参半。
有人说他冷酷专权,有人说他铁血手腕,也有人说他……好男风。
“过来。”他忽然说。
我一怔,依言走近几步。
他指了指旁边的座位:“坐。”
我忐忑坐下。
他拿起酒壶,给我面前的空杯倒了一杯酒。
琥珀色的液体,香气醇厚。
“尝尝。江南送来的梨花白。”
我受宠若惊,端起酒杯,小心抿了一口。
清冽甘甜,带着淡淡的梨花香。
“好酒。”我由衷赞道。
“赈灾钱粮的事,你办得不错。”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,“想要什么奖赏?”
我放下酒杯,正色道:“下官分内之事,不敢居功。”
他晃着酒杯,没看我。
“分内之事?”他语气意味不明,“那本画册,也是你的分内之事?”
我一口酒差点呛住。
“王爷!那真的……”
“行了,”他打断我,“本王没怪你。”
我愣住。
他抬眼,目光落在我脸上。
烛火在他眼底跳跃。
“沈知微,”他声音低了些,“本王问你,若有人非议你我,你当如何?”
我心脏狂跳起来。
这问题……太危险了。
“下官……下官清者自清!”我挺直脊背。
“清者自清?”他重复一遍,忽然笑了。
笑得有些嘲弄。
“若这世上,清者自清有用,还要律法做什么?还要本王……做什么?”
他放下酒杯,身体微微前倾。
距离拉近。
他身上清冽的气息混合着酒香,将我笼罩。
“本王教你一个道理,”他看着我,眼神深邃如潭,“流言如刀,避之不及时,不如……”
他顿了顿,一字一句。
“握刀在手,为我所用。”
我心头剧震。
握刀在手,为我所用?
他是在教我……利用流言?
“王爷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赈灾钱粮虽有着落,但后续调拨、分配、监管,千头万绪。”他靠回椅背,语气恢复平淡,“户部上下,盘根错节。你一个新晋主事,人微言轻,推行条陈,必然阻力重重。”
我点头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
“但若……”他指尖轻轻敲着桌面,“若本王对你,格外‘青眼有加’呢?”
我猛地抬头看他。
他神色平静。
“若满朝皆知,你沈知微,是本王看重的人呢?”
我明白了。
他是要用这荒谬的流言,给我披上一层“摄政王亲信”的保护色!
让那些想给我使绊子的人,投鼠忌器!
“王爷……”我喉咙发干,“这……有损王爷清誉……”
“清誉?”他再次嗤笑,带着不屑,“本王何时在乎过那个?”
他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
“沈知微。”
“下官在。”
“江南水患,数十万灾民,等米下锅。”他看着我,目光如炬,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,“本王要你,放开手脚,把差事办好。谁敢阻你,便是阻本王。”
“这‘流言’,”他唇角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,“便是你的护身符。”
“懂了吗?”
我看着他。
看着他眼底映出的烛火。
看着那张冷峻脸上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绝。
还有……那深藏眼底的,对灾民的忧切。
我端起酒杯,站起身,深深一揖。
“下官,明白了。”
“谢王爷……赐符。”
我仰头,将杯中梨花白,一饮而尽。
酒液滚烫。
烧灼着喉咙。
也点燃了胸腔里的一团火。
自那晚王府夜宴后,事情起了微妙的变化。
我拿着齐珩亲自批下的条陈,在户部推行“以工代赈”和“工票制”。
果然遇到了阻力。
几个老资格的员外郎,明里暗里使绊子。
不是推诿人手不够,就是说账目难算。
搁以前,我一个新人,只能干着急。
但现在……
我只需在议事时,状似无意地提起一句:“此事王爷催问过进度。”
或者,在散衙后,“恰好”绕道去一趟摄政王府。
哪怕只是在门房喝杯茶。
第二天,那些拖延的公文,就会神奇地出现在我案头。
效率高得惊人。
李肃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“高!实在是高!知微!你这‘狐假虎威’……不对,‘摄政王威’,玩得炉火纯青啊!”
我翻看着刚送来的河道民夫名册,头也不抬。
“别瞎说。都是为朝廷办差。”
“是是是!”李肃凑过来,挤眉弄眼,“不过兄弟,你跟王爷……真没什么?”
我笔尖一顿。
脑海里闪过那晚花厅,烛光下他深邃的眼。
“没有。”我斩钉截铁。
李肃一脸“我懂”的表情:“明白!明白!低调!要低调!”
我懒得理他。
流言这把刀,确实好用。
但也烫手。
这天,我去工部找张尚书核对河道图纸。
刚走到回廊,就听见几个工部官员在凉亭里闲聊。
“……真的假的?王爷真看上那个沈知微了?一个小小主事?”
“千真万确!我小舅子在王府当差!说前几日王爷设宴,就只带了沈知微一人作陪!席间还亲自给他倒酒!”
“嘶——王爷亲自倒酒?这……这恩宠……”
“何止!听说王爷还当着那些富商的面,让沈知微坐他旁边!那位置,以前可是首辅大人坐的!”
“我的天!怪不得户部那帮老油条现在对沈知微客客气气的!”
“啧啧,真是人不可貌相!你说那沈知微,细皮嫩肉的,还真有几分……嗯?”
一阵心照不宣的低笑传来。
我站在廊柱后,手脚冰凉。
虽然早有心理准备。
但亲耳听到这些污言秽语,还是像被当众扇了一耳光。
脸上**辣的。
我深吸一口气,压下心头的屈辱和怒火。
握紧手里的图纸,准备转身离开。
“咳!”
一声不高不低的咳嗽声,自身后响起。
凉亭里的谈笑声戛然而止。
那几个工部官员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,惊恐地看向我身后。
我僵硬地转过身。
齐珩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。
一身玄色常服,面无表情。
他身后跟着两个内卫。
气氛瞬间降至冰点。
那几个工部官员脸都吓白了,扑通跪倒在地。
“王……王爷!”
齐珩没看他们。
目光落在我身上。
“沈大人。”
“下官在。”我垂首,声音有些发紧。
“图纸拿来了?”
“是,正要送去给张尚书。”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,目光这才转向凉亭里那几个抖如筛糠的官员。
眼神冰冷。
“朝廷俸禄,”他开口,声音不高,却像带着冰碴,“是养你们来嚼舌根的?”
“王爷饶命!下官知错!下官再也不敢了!”几人磕头如捣蒜。
“每人罚俸半年。”齐珩语气平淡,“再让本王听到一句闲言碎语,这舌头,就别要了。”
“谢王爷开恩!谢王爷开恩!”几人如蒙大赦,连滚爬爬地跑了。
回廊里只剩下我和齐珩,还有他身后的内卫。
空气有些凝滞。
我低着头,盯着自己的鞋尖。
刚才那些话,他肯定也听到了。
他会怎么想?
会觉得我给他惹麻烦了吗?
“吓到了?”他忽然问。
我摇头:“没有。流言蜚语,下官……习惯了。”
“习惯?”他走近一步。
那股清冽的气息又笼罩过来。
“习惯被人指着脊梁骨,说你是靠……裙带关系上位?”
他语气平淡,说出的话却像刀子。
我猛地抬头看他。
对上他深不见底的眼。
“下官问心无愧!”我挺直脊背,声音有些发颤,却带着倔强,“下官凭本事为朝廷效力!凭良心为灾民做事!至于他人如何置喙,下官管不了,也不想管!”
他看着我。
看了很久。
久到我以为他要发怒。
他却忽然抬手。
微凉的指尖,轻轻拂过我眼角。
那里,有点控制不住的湿意。
“委屈了?”他声音低了些。
我别开脸,躲开他的触碰。
“没有。”
他收回手,指尖捻了捻。
“沈知微。”
“下官在。”
“抬起头来。”
我吸了口气,抬起头,迎上他的目光。
“记住本王的话,”他看着我,一字一句,清晰有力,“你凭本事挣来的位置,没人能夺走。本王给你的‘护身符’,不是让你用来受气的。”
他顿了顿,语气带上几分冷厉。
“是让你拿来,打人的。”
我心头一震。
“若再有人敢当面辱你,”他目光扫过我紧握的拳头,“你便打回去。打不过,来找本王。”
“天塌下来,”他最后说,“本王给你顶着。”
说完,他不再看我,转身带着内卫走了。
玄色的衣袍消失在回廊尽头。
我站在原地。
指尖还残留着他触碰过的微凉。
耳边回响着他那句“本王给你顶着”。
胸腔里那颗心,在屈辱和愤怒之后,被一种难以言喻的酸胀填满。
像是冰封的河面,被投入了一块滚烫的石头。
咔嚓一声。
裂开了一道缝隙。
流言这把刀,握在手里,似乎没那么烫了。
日子在忙碌和流言中滑过。
江南的河道在数万民夫的努力下,渐渐疏通。
“工票制”推行顺利,民夫们能及时拿到现钱或米粮,干劲十足。
灾情得到缓解。
朝堂上,对齐珩的质疑声也小了很多。
我那本“护身符”,似乎也渐渐褪色。
直到那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