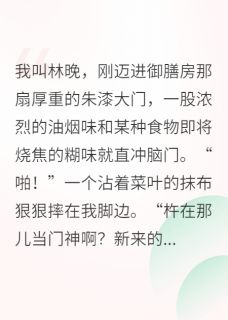我叫林晚,刚迈进御膳房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,
一股浓烈的油烟味和某种食物即将烧焦的糊味就直冲脑门。“啪!
”一个沾着菜叶的抹布狠狠摔在我脚边。“杵在那儿当门神啊?新来的?
”一个穿着油腻腻深褐色短打、腰围几乎是我两倍的中年胖男人,叉着腰冲我吼,
唾沫星子差点喷我脸上,“没看见都火烧眉毛了吗?赶紧的,去把那堆萝卜皮削了!
削干净点,要是敢浪费一丁点,仔细你的皮!”他叫王管事,嗓门大得像打雷,
是整个御膳房底层杂役的头儿。我缩了缩脖子,不敢吭声,
赶紧小跑到角落那堆成小山的萝卜旁边,拿起一把豁了口的破刀。手刚碰到冰凉的萝卜,
旁边就传来压抑的、带着哭腔的议论。“完了完了……贵妃娘娘那只雪狮子猫,
今儿又一口没吃……”“这都第三天了!再这样下去,咱们的脑袋都得搬家!
”“御膳房最好的鱼脍、最嫩的鸡胸肉丝、羊奶……连御赐的贡品蜜饯都试过了,
那猫祖宗就是闻都不闻一下!”“听说娘娘急得摔了好几套茶具了,再想不出法子,
咱们……咱们真就……”恐慌像冰冷的潮水,瞬间淹没了这个热气腾腾的角落。
削萝卜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。我,林晚,刚通过选秀入宫的小宫女,
被分到这号称“油水多、是非更多”的御膳房打杂,还不到三天。
本以为能靠着前世在五星级酒店后厨摸爬滚打十几年的经验,在这里混口安稳饭吃,
慢慢往上爬。哪知道,安稳饭没吃着,杀身之祸先悬在了头顶。贵妃的猫不吃东西?
这罪名扣下来,我们这些最底层的杂役,绝对是最先被推出去顶缸的炮灰。心砰砰狂跳,
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前世做私房菜馆时,
也遇到过不少被主人宠坏、挑食挑到极致的猫主子。
对付这种毛孩子……一个极其大胆、甚至可以说是在找死边缘疯狂试探的念头,
猛地蹿了出来。我猛地放下豁口刀,在围裙上胡乱擦了擦手心的冷汗。“王……王管事!
”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发颤,但在死寂的恐慌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王管事正焦躁地揪着自己稀疏的头发,闻言凶神恶煞地瞪过来:“叫什么叫!萝卜皮削完了?
”“没……没有。”我深吸一口气,强迫自己站直,“但是……奴婢……奴婢或许有法子,
能让贵妃娘娘的猫……吃点东西。”整个嘈杂的角落,瞬间安静得可怕。所有目光,
像探照灯一样,“唰”地全集中在我身上。有惊疑,有嘲讽,
更多的像是在看一个不知死活的疯子。王管事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,上下打量我,
像在掂量一块砧板上的肉:“你?新来的毛丫头?你懂个屁!滚回去削你的萝卜皮!
”“奴婢以前……在家乡照顾过不少猫狗,知道一些它们爱吃的偏门东西。”我硬着头皮,
语速飞快,“只需要一点点材料,一点点时间!万一……万一成了呢?
总比干等着掉脑袋强啊!”“偏门东西?”旁边一个尖嘴猴腮的瘦高个嗤笑一声,
“我说小丫头,这可是贵妃娘娘的心肝宝贝!你敢给它乱吃东西?吃出毛病来,
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?王管事,别听她胡咧咧!”这人是赵三,王管事的狗腿子,
平时最爱欺负新人。王管事脸上阴晴不定。贵妃那边的压力越来越大,他额头的汗就没停过。
他盯着我,眼神里全是挣扎和怀疑:“你……你要什么材料?说!”成了!第一步赌对了!
“一点点新鲜的小鱼,巴掌大的就行,两条!一点粗盐,一点点干净的猪油,一点点……呃,
厨房角落里那种晒干的紫苏叶子!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把握,“就这些!很快!
”“就这?”王管事狐疑更深。“对!就这些!”我用力点头,
“请王管事给奴婢一个机会!”死马当活马医吧。王管事烦躁地一挥手:“去去去!赵三,
带她去小库房拿!快着点!要是弄砸了……哼!”那声冷哼,让我后背发凉。
小库房阴暗潮湿,弥漫着灰尘和干货混杂的气味。赵三一边不耐烦地翻找,
一边阴阳怪气:“小丫头片子,别以为耍点小聪明就能出头!御膳房的水深着呢,
小心淹死你!”我没理他,飞快地挑了两条最不起眼但还算新鲜的小杂鱼,抓了一小撮粗盐,
用油纸包了一小勺凝固的猪油,又在角落里找到一小把落满灰的干紫苏叶。
回到那个充满绝望气息的角落,我找了一个最不起眼的、几乎废弃的小灶眼。点火,
烧热小小的铁锅。刷上薄薄一层猪油。把两条小鱼擦干水分,用粗盐在表面细细抹了一层,
轻轻拍打,然后放进微热的锅里。“嗤啦……”极细微的油煎声响起。香气?几乎没有。
只有一点点蛋白质受热的味道。周围伸长脖子看热闹的杂役们,脸上失望和嘲讽更浓了。
“就这?”“比咱们做的鱼脍差远了!”“白费功夫!”赵三更是抱着胳膊冷笑。
我不为所动,专注地盯着锅里的小鱼。火候是关键!不能煎老,
要保持鱼肉的弹性和一丝丝湿润感。两面煎到微微金黄,立刻夹出来,放在干净的案板上。
然后,拿起那几片干巴巴的紫苏叶,用手指捻碎成细末,均匀地洒在还冒着热气的鱼身上。
最后一步,我拿起擀面杖——不是擀面,而是用侧面,对着煎好的小鱼,
用力地、一下一下地捶打!“嘭!嘭!嘭!”沉闷的捶打声在安静的厨房里格外突兀。
“她在干嘛?捣鱼酱?”“疯了吧?”鱼肉在捶打下,纤维断裂,变得更加松散,
紫苏的独特香气随着热气被激发出来,与鱼肉本身的鲜味奇异地融合在一起,
形成一种……非常原始、非常纯粹的肉香。这香气并不浓烈,
甚至比不上旁边灶上炖着的高汤。
但就是这股带着点野性的、混合着焦香、咸鲜和紫苏特殊清香的奇异味道,
丝丝缕缕地飘散开。捶打到鱼肉变成细碎的丝状,带着微微的韧劲。我飞快地抓起一小撮,
在掌心团成一个小小的、指头肚大小的丸子。“好了!
”我捧着那个其貌不扬、还带着点温热的鱼丸,声音都在抖,“快!快送去!趁热!
”王管事半信半疑,像捧着一颗随时会炸的炸弹,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小丸子,
用个精致的小碟子装了,亲自小跑着送了出去。等待的时间,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
厨房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没人说话,没人干活。削萝卜的刀停在半空,
烧火的柴火噼啪作响格外刺耳。赵三凑到我身边,压着嗓子,阴恻恻地说:“小丫头,
等着吧。贵妃娘娘要是怪罪下来,第一个就拿你开刀!”我手心全是汗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
强迫自己镇定。不知过了多久,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!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跑进来的是贵妃宫里一个面生的小太监,脸上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狂喜,
尖着嗓子喊:“吃了!吃了!雪球儿(那猫的名字)把那丸子全吃了!还……还舔了碟子!
娘娘高兴坏了!问是谁做的点心?有赏!重重有赏!”“轰!”厨房里炸开了锅!
“我的老天爷!真成了?”“这丫头神了!”“有救了!我们有救了!
”王管事跟在小太监后面冲进来,那张油腻的胖脸因为激动涨得通红,小眼睛瞪得溜圆,
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金元宝!“林……林晚!是你!真是你!快!
快跟我去见贵妃娘娘派来的公公!娘娘有赏!
”巨大的喜悦和劫后余生的虚脱感瞬间击中了我,腿一软,差点没站稳。
贵妃娘娘的赏赐很实在:十两雪花银,一支成色不错的素银簪子。
钱和簪子被王管事“代为保管”了,美其名曰“新人拿着不安全,先帮你存着”。我懂。
御膳房的规矩,新人得“孝敬”。但我真正得到的,
比那点赏赐重要得多——我在这个吃人的御膳房,第一次拥有了名字,
而不仅仅是一个代号“新来的”。更重要的是,我有了一个机会。
王管事大概是觉得我有点“歪才”,或者怕下次再遇到这种要命的事没人顶缸,
居然把我从削萝卜皮的杂役堆里拎了出来,
扔给了一个负责做“下等人”伙食的老御厨——陈砚。陈师傅五十多岁,瘦得像根竹竿,
背有点驼,脸上皱纹深刻,眼神浑浊,总是沉默寡言。他负责的区域,
是整个御膳房最边缘、最不起眼的一个灶台,
专门给宫里最低等的太监、宫女、杂役们做大锅饭。食材?
歪瓜裂枣的萝卜土豆、碎米、陈米……甚至偶尔有些主子们挑剩下、嫌弃部位不好的肉骨头。
味道?能煮熟、能吃、吃不死人就行。用赵三那帮人的话说:“喂猪的都比这强!
”陈师傅大概也是心如死灰,每天机械地挥动大铲子,
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倒进巨大的铁锅里,加水,加盐,咕嘟咕嘟熬煮。
蒸笼里永远是干硬粗糙、能硌掉牙的杂粮窝头。我第一天报到,
就被那股混合着烂菜叶和猪油哈喇味的“食堂气息”熏得够呛。陈师傅抬眼皮看了我一眼,
浑浊的目光没什么波动,用沙哑的嗓子指了指角落一堆蔫了吧唧的白菜帮子:“去,
把那堆烂叶子切了。仔细点,别浪费。”“是,陈师傅。”我挽起袖子,拿起刀。
切着毫无水分的白菜帮子,看着锅里那令人毫无食欲的灰绿色糊状物,
前世那些追求食材本味、讲究火候功力的职业习惯在疯狂叫嚣。这玩意儿,真的能吃?
但我知道,现在不是挑剔的时候。这里是起点,也是我的机会。
中午开饭的铜锣“哐哐”敲响。一群群穿着灰扑扑衣服的低等宫人端着破口的粗瓷碗,
排着长队,面无表情地走到大锅前。打饭的杂役面无表情地舀起一大勺糊糊,
“啪”地扣进他们的碗里,再塞一个硬邦邦的窝头。我站在陈师傅身后,悄悄观察。
大多数人麻木地端着碗,找个角落蹲下,机械地吞咽着那毫无滋味的糊糊,
啃着能当武器的窝头。眼神空洞,仿佛吃的不是食物,只是维持生命的燃料。
偶尔有几个年轻的,会看着碗里的东西皱皱眉,
小声抱怨两句:“又是这个……猪食啊……”“小声点!有的吃就不错了!还想跟主子们比?
”抱怨声很快被淹没在沉默的咀嚼声里。心口有点堵。晚上,躺在通铺大炕的角落,
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鼾声和磨牙声,我失眠了。前世,我热爱烹饪,
坚信食物是能传递温暖和力量的东西。可在这里,食物成了最冰冷、最没有尊严的符号。
不行。就算是最底层的伙食,就算只有边角料,我也得让它有点人味儿!第二天,
我主动揽下了处理那堆没人要的猪皮和肥膘的活。“陈师傅,这些……能给我吗?
”我指着角落里那堆腥臊油腻的下脚料。陈师傅撩起眼皮,有些诧异:“那玩意儿腥得很,
熬油都嫌味重,你要它干嘛?”“奴婢……奴婢试试看能不能做点别的。”我小声说。
陈师傅沉默了一下,挥挥手:“随你。别糟蹋太多柴火就行。”成了!
我把那些猪皮仔细刮掉残留的毛发和肥油,清洗干净,丢进大锅里,
加冷水、姜片、一点点便宜的黄酒(从库房角落里翻出来的,快过期了),
大火烧开撇去浮沫,转小火慢慢熬煮。猪皮在锅里翻滚,渐渐变得透明软糯,
汤色也一点点变白。浓郁的、属于胶原蛋白的香气,开始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弥漫开来。
这香味跟御膳房主流的高汤、肉香完全不同,它更质朴,更……接地气。
引得附近几个洗菜的小宫女频频侧目。熬了足足两个时辰,汤汁变得浓稠雪白,像融化的玉。
我把煮得筷子一戳就烂的猪皮捞出来,切成细丁,又倒回浓汤里。没有高级的瑶柱火腿,
我就把昨天偷偷留下的一小把虾米(也是边角料,碎得不行)用小火焙干,碾成粉末。
再撒上一大把切得碎碎的、脆生生的腌萝卜丁——这也是下饭菜里没人爱吃的部分,
嫌太咸太硬。最后,加入适量的盐,一点点能提鲜的酱油。
一锅改良版的“边角料猪皮冻羹”诞生了!晶莹剔透的浓汤里,
悬浮着软糯的猪皮丁、脆爽的萝卜丁,金黄的虾米粉点缀其间。
浓郁的胶质香气混合着虾米的鲜和萝卜丁的咸鲜脆爽,直往鼻子里钻。中午开饭。
当那锅灰绿色的糊糊旁边,
多了一大桶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、看起来甚至有点“晶莹剔透”的新东西时,
排队的人都愣住了。打饭的杂役也懵了,看看我,又看看陈师傅。
陈师傅浑浊的眼睛盯着那桶冻羹,鼻子微微抽动了一下,没说话,只是对我点了点头。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?”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小太监,端着碗,迟疑地问。“猪皮冻羹,
新添的,尝尝?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小太监犹豫了一下,
看着那诱人的色泽和香气,还是把碗递了过来。我舀了一大勺,
浓稠的羹汤颤巍巍地落入粗瓷碗里,猪皮丁和萝卜丁清晰可见。那小太监端着碗,走到一边,
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。下一秒,他的眼睛猛地瞪大了!脸上那种惯常的麻木和疲惫,
像被什么东西击碎了!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又喝了一大口,然后顾不上烫,开始狼吞虎咽。
最后,连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!吃完,他意犹未尽地砸吧着嘴,眼神亮晶晶地看向大锅那边,
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再去排一次队。这个反应,像一颗火星掉进了干草堆。“给我来一碗!
”“我也要!我也要那个!”“闻着好香啊!”队伍瞬间骚动起来,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,
拼命往前挤,目标明确地指向那桶猪皮冻羹!负责打糊糊的杂役那边,瞬间门可罗雀。
那一桶冻羹,以惊人的速度被瓜分一空。没抢到的人,看着空桶,满脸的失落和懊恼,
连带着看那碗灰绿色的糊糊,眼神都更加嫌弃了。而吃到的人,
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、属于“满足”的神情。有人小声交谈,声音里带着点鲜活气:“天,
真好吃!又鲜又滑!”“里面的小疙瘩(猪皮丁)糯糯的,脆脆的(萝卜丁)也好吃!
”“好久没吃到这么有滋味的东西了……”陈师傅站在角落里,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
他那张刻板严肃的脸上,似乎有什么东西松动了一下。他走到空桶边,拿起勺子,
刮了刮桶壁上残留的一点羹汤,送进嘴里。他咂摸了很久,浑浊的眼睛里,
闪过一道极其微弱的光。然后,他什么也没说,背着手,慢慢走回了他的灶台。但从那天起,
我处理边角料的权限,似乎被默许放大了。我开始变着花样折腾那些“垃圾”。
长得歪歪扭扭的土豆萝卜,蒸熟捣成泥,加点盐和仅有的、味道很冲的廉价猪油,
做成简单却喷香的土豆萝卜泥饼,在铁锅上烙得两面金黄焦脆。发黄的白菜帮子,
细细切成丝,用一点点盐杀出水分,挤干。没有粉丝,就把碎米磨成浆,蒸成薄薄的米皮,
切丝冒充。
上蒜末(也是边角料里扒拉出来的小蒜头)、一点点醋(从做醋鱼的灶台讨来的边角料醋),
拌成酸辣口的“假拌粉”。剔得光溜溜的肉骨头,敲碎了丢进大锅里,
加上各种同样被嫌弃的蔬菜根茎(萝卜头、芹菜根、白菜疙瘩),小火慢炖上大半天,
熬成一锅浓郁醇厚、撒点粗盐就鲜掉眉毛的骨头蔬菜汤。我用尽前世所有的经验和智慧,
把那些被人弃如敝履的边角料,点石成金。陈师傅的沉默,成了最大的支持。他不再干涉我,
有时甚至会把他分到的一些同样不怎么样的材料,默不作声地推到我这边。
我们的“下等人食堂”,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每天中午,
那桶热气腾腾、散发着诱人香气的主食旁边(有时是浓羹,有时是金黄的烙饼,
有时是酸辣开胃的拌菜),总是最先被抢光。排队的人群里,开始有了小声的交谈和期待。
“今天林晚姑娘又做什么好吃的了?”“昨天那个骨头汤真绝了,我泡着窝头吃,
连碗都舔了!”“嘘……小点声,别给林姑娘惹麻烦……”麻烦,其实一直没断过。
赵三那伙人,眼红得要滴血。凭什么一个刚来的小丫头,用着最烂的料,
却成了那些低等宫人嘴里的“林晚姑娘”?连带着那个半死不活的陈老头,
都好像有了点人气?王管事虽然拿走了我的赏银,但他更看重的是他自己的位置和油水。
我搞出的这点小水花,暂时还没触及他的核心利益,所以他只是冷眼旁观。但赵三不同。
他就是条疯狗,见不得别人好,尤其见不得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人冒头。他开始找茬。
先是故意把分给我们这边的食材弄得更差、更少,或者掺杂很多泥沙烂叶。陈师傅皱着眉,
没说话。我默默地把那些烂叶挑出来,泥沙多的食材反复淘洗。后来,他趁我不注意,
往我准备用来熬汤的骨头堆里,倒了一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、散发着恶臭的泔水。那天,
我差点没控制住,想抓起那根臭骨头砸到他脸上。但我忍住了。
我把那堆被污染的骨头全扔了,重新去库房门口蹲守,软磨硬泡,从运泔水的老太监那里,
用帮他收拾半天泔水桶的代价,换了几根还算干净的、准备丢弃的羊蝎子骨。
那天中午的羊蝎子萝卜汤,香味飘得格外远。连一些路过的、等级稍高点的宫女太监,
都忍不住驻足,好奇地张望。赵三气得脸都绿了。硬的不行,他就来阴的。
他开始在低等宫人里散播谣言。“知道那丫头用的什么料吗?都是主子们不要的垃圾!
泔水桶里捞出来的!”“那猪皮冻?呸!谁知道是什么脏东西熬的?
吃坏了肚子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!”“还有那些肉骨头,啧啧,
听说……是从乱葬岗野狗嘴里抢来的呢!”谣言像毒草一样悄悄蔓延。果然,
第二天中午排队打饭的人,少了一些。有些人端着碗,
看着那锅热气腾腾的杂菌豆腐汤(菌子是雨后我在御花园边缘没人要的树根下采的野蘑菇),
眼神里充满了犹豫和恐惧。一个平时挺活跃的小宫女,端着碗,迟迟不敢上前,
小声问:“林……林晚姑娘,这汤……干净吗?我……我听说……”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环顾四周,赵三躲在人群后面,抱着胳膊,脸上挂着恶毒而得意的笑。
陈师傅停下了搅拌汤锅的大勺,沉默地看着我,浑浊的眼底有一丝担忧。怎么办?解释?
说我没用泔水?说我的食材来源?只会越描越黑。在这个等级森严、流言杀人的地方,
我一个底层小宫女的话,有谁会信?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僵持时刻,
一个穿着体面些、管事姑姑模样的中年宫女,带着两个小宫女,径直走到了我们的汤锅前。
排队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,自动分开一条路。是浣衣局的刘姑姑!
她管着宫里好几十号洗衣宫女,算是有点小权力的女官。她为人严厉,但还算公正,
在底层宫人里颇有威信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赵三脸上的得意更浓了。刘姑姑没看任何人,
直接走到汤锅边,拿起旁边干净的勺子,舀了小半勺汤,吹了吹,仔细地尝了一口。
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刘姑姑细细品着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她又舀了一点汤里的杂菌和豆腐,
慢慢咀嚼。时间仿佛凝固了。终于,她放下勺子,看向我,声音不大,
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:“汤,很鲜。豆腐滑嫩,菌子也新鲜干净。”她顿了顿,
目光锐利地扫过噤若寒蝉的人群,“我浣衣局十几个丫头,连着喝了三天你们这儿的汤,
没一个闹肚子的。身子骨反而比之前有劲了,洗的衣服都多了。”她最后的目光,
有意无意地落在了赵三藏身的方向,带着警告:“有功夫嚼舌根子,
不如想想怎么把自己的活干好。再让我听见有人乱传些没影儿的脏话,污了大家的伙食,
别怪我按宫规处置!”说完,她对我微微颔首,转身带着人走了。静!死一般的寂静后,
是轰然的议论!“听见没!刘姑姑都说好!”“浣衣局的人喝了三天都没事!”“我就说嘛!
林晚姑娘做的东西,看着就干净!”“哪个黑心肝的乱嚼舌根?”人群重新涌动起来,
争先恐后地涌向汤锅,生怕抢不到。刚才还在犹豫的小宫女,也红着脸赶紧把碗递了过来。
赵三那张脸,瞬间由绿转黑,像被狠狠抽了几巴掌,灰溜溜地挤出了人群,消失不见。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后背的冷汗都快浸透了里衣。看向刘姑姑离去的方向,
心里充满了感激。陈师傅默默地把大勺递给我,自己转身去揉面了。
但我看见他微微佝偻的背,似乎挺直了一点点。这场小小的风波,像一块试金石。
不仅没打垮我,反而让“林晚”这个名字,在御膳房最底层,甚至像浣衣局这样的地方,
悄悄扎下了根。大家看我的眼神,不再是看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杂役,
而是多了几分信赖和亲近。连带着对沉默寡言的陈师傅,也多了几分尊重。我知道,
这仅仅是个开始。赵三不会善罢甘休,王管事的心思也难测。但至少,我在这里,
有了第一块小小的、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。日子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和油烟蒸腾中滑过。
靠着那些化腐朽为神奇的边角料料理,我在底层宫人里攒下了一点人缘。
偶尔会有小宫女偷偷塞给我一小块干净的帕子,或者小太监帮我多扛一袋重物。
陈师傅依旧沉默,但分给我的活计,渐渐多了些“技术含量”——比如让我帮忙看火候,
或者处理一些需要精细刀工的食材。他偶尔会在我做菜时,站在旁边看一会儿,
浑浊的眼睛里偶尔闪过一丝难以捕捉的光。我知道,他在观察,在评估。
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,一场更大的风波,裹挟着秋雨,席卷了整个御膳房。
掌管御膳房的大总管高公公,突然病倒了,来势汹汹,据说连着几天高烧不退,水米难进,
人瘦脱了形。太医开了方子,但药灌下去,人还是昏昏沉沉,眼看着就不行了。
宫里主子们虽然不至于为一个奴才的病多费心,但高公公的位置太关键。他一倒,
整个御膳房的运转都受到了影响,好几处给主子们预备的精细点心出了岔子,
惹得几位娘娘不快。上面发了话:御膳房自己想办法!务必让高公公尽快好起来,
至少得能开**代差事!否则,从上到下,都吃不了兜着走!压力层层下压,
最终砸在了几个掌勺大御厨和王管事头上。几位大御厨使出浑身解数,
各种滋补药膳、精细羹汤流水似的往高公公养病的偏殿送。
燕窝粥、人参鸡汤、鲍汁烩辽参……都是顶金贵的东西。可送进去多少,
原封不动端出来多少。负责伺候的小太监哭丧着脸:“公公还是咽不下去,勉强喂进去一点,
转头就吐了……说嘴里没味,心里发腻,
看见这些油星子就想吐……”掌勺的御厨们急得嘴上起泡。这些珍贵的食材,不仅没见效,
反而像在打他们的脸。王管事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,在御膳房里团团转,逮谁骂谁。“废物!
一群废物!养你们干什么吃的!连碗开胃的汤都做不出来吗?
”他肥胖的身体因为焦躁而抖动,唾沫星子乱飞。就在这时,
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:“王管事,您急什么呀?咱们御膳房,
不是藏着一位‘化腐朽为神奇’的高人吗?连泔水……哦不,
连边角料都能做出山珍海味的味儿来,说不定,就有法子让高公公开开胃呢?”是赵三!
他抱着胳膊,斜睨着角落里正在处理一堆老姜的我,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恶意和幸灾乐祸。刷!
所有的目光,瞬间聚焦在我身上。有惊愕,有同情,更多的,是等着看好戏的冷漠。
王管事的小眼睛“嗖”地盯住了我,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,
又像是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替罪羊。“林晚!”他几步冲到我面前,
油腻的胖脸几乎要贴上我的鼻尖,“赵三说的对!你!去!给高公公做点开胃的东西!
做好了,重重有赏!做不好……”他冷笑一声,后面的话不言而喻。
巨大的压力瞬间将我笼罩。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。给大总管做吃食?
还是在他病重厌食的时候?这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!做得好,是僭越,是打几位大御厨的脸。
做不好,或者万一吃出点问题……我就是现成的背锅侠,死无葬身之地!赵三这招,太毒了!
陈师傅停下了切菜的手,担忧地看了我一眼,嘴唇动了动,最终还是没出声。我知道,
这种时候,他帮不了我。看着王管事那不容置疑的凶狠眼神,看着赵三那恶毒得意的笑容,
看着周围那些或冷漠或同情的目光……退无可退。我深吸一口气,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,
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高公公的症状:高烧后体虚,脾胃极弱,厌油腥,看到滋补品就恶心。
嘴里发苦,没味道,
只想吃点清爽的、能唤醒味蕾的东西……前世积累的经验在脑海中飞速翻腾。
病人……虚弱……厌油腥……需要开胃……清爽……有了!“王管事,
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,“奴婢需要一些东西:新鲜的白萝卜半根,
要水头足的。最嫩的鸡胸肉一小块。老姜一小块。
还有……一小撮咱们做酸梅汤用的、最次的乌梅干,两三颗就行。
再要一点干净的雪水或者最清的井水,一点点最普通的粗盐。”我报出的东西,
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白萝卜?鸡胸肉?乌梅干?雪水?这寒酸得连边角料都不如的清单,
跟御厨们那些燕窝人参比起来,简直是云泥之别!“就……就这些?
”王管事一脸难以置信,甚至有点被戏弄的恼怒,“你耍我呢?”“王管事,
高公公现在虚不受补,看见油星就反胃。这些东西看着简单,或许能合公公的胃口。
”我迎着他的目光,语气坚定,“请管事给奴婢一次机会。若不成,奴婢甘愿领罚!
”王管事死死盯着我,像是在权衡利弊。最终,对上面压力的恐惧压倒了一切。
他一跺脚:“好!就依你!赵三,去库房给她拿!要快!”赵三撇着嘴,不情不愿地去拿了。
很快,我要的东西都摆在了眼前:半截水灵的白萝卜,一小块还算新鲜的鸡胸肉,
几颗干瘪发黑的乌梅干,一小罐清澈的雪水,一点粗盐。
我找了一个最小号的、极其干净的砂锅。动作麻利地将白萝卜去皮,切成极细极细的丝,
放入清冽的雪水中浸泡着,去除生涩气。鸡胸肉去掉筋膜,用刀背细细捶打成茸,
同样用一点雪水澥开,搅打上劲,变成细腻的鸡茸糊。老姜去皮,只用最嫩的心儿,
切成细如发丝的姜丝。那几颗乌梅干,用温水泡软,仔细剔去核,只取一点点果肉,
切成更细碎的末。砂锅置于最小最小的火眼上,倒入剩余的雪水,
加入姜丝和那一小撮乌梅末,烧开。水沸后,转成几乎看不到火苗的文火,
让水保持将沸未沸的状态。用筷子夹起浸泡好的萝卜丝,沥干水分,轻轻抖散,
缓缓地、均匀地撒入这微沸的“底汤”中。雪白的萝卜丝在清澈的汤水中缓缓舒展、下沉,
像初冬的第一场细雪。然后,用一个小漏勺,舀起细腻的鸡茸糊,
极其轻柔、极其缓慢地淋入汤中。鸡茸遇热迅速凝固,
变成一朵朵极其细小、洁白如云的鸡茸花,轻盈地漂浮在汤面上,与萝卜丝交织。最后,
只调入一点点,真的只是一点点的粗盐。整个过程,我全神贯注,屏住呼吸,
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。厨房里鸦雀无声,只有砂锅里极其细微的“咕嘟”声。
没有浓烈的香气,只有一股极其清淡、若有似无的,
混合着萝卜清甜、乌梅微酸、姜丝辛香的独特气息,丝丝缕缕地飘散出来。
这气息干净得如同山间清泉,瞬间涤荡了御膳房浓郁的油腻。
一碗汤被小心翼翼地盛入细瓷碗中:汤色清澈见底,几乎透明。
洁白的鸡茸花和晶莹的萝卜丝均匀悬浮,点点姜丝和深色的乌梅末点缀其间,
像一幅写意的水墨画。王管事亲自端着这碗寒酸到极致的汤,忐忑不安地送往偏殿。
等待的时间,比上次贵妃的猫吃食时更加煎熬。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炸。
赵三抱着胳膊,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冷笑:“哼,装神弄鬼!就这清汤寡水,
给高公公漱口都不配!等着挨板子吧!”其他御厨也纷纷摇头,显然不抱任何希望。
陈师傅坐在他的小马扎上,低着头,看不清表情。不知过了多久,
就在我几乎要站不住的时候,外面传来一阵急促而凌乱的脚步声!
王管事几乎是连滚爬爬地冲了进来!他满脸通红,小眼睛瞪得溜圆,
因为跑得太急而呼哧带喘,脸上是一种混合了狂喜、震惊和难以置信的扭曲表情!